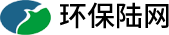康保成戏曲究竟是演人物还是演行当
时间:2020-05-08 23:55:43 来源:黄石环保厂家 浏览量:2
邹元江在他的专著和系列论文中,对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与表演理论提出过严苛的批评。邹元江点名批评的,除了梅兰芳及其“梅党”之外,还有一大批戏曲表演艺术家和理论家,如程砚秋、周信芳、田汉、欧阳予倩、张庚、黄佐临、阿甲、李紫贵、刘厚生等人。邹元江的批评若成立,不仅近百年来形成的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艺术表演体系,而且几百年来形成的中国戏曲表演体系都将坍塌。或许是由于问题过于重大,也或许是由于是非不难判明,故学术界屑于回应者并不多。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梅兰芳曾提出戏曲表演应当把“很切合剧情地扮演那个剧中人”与“把优美的舞蹈加以体现”当成自己的“两重任务”。而在邹元江看来,所谓“两重任务”只是梅先生“虚设的”,戏曲并不扮演人物,而是“表演行当”。那么,既然“两重任务”并不存在,戏曲难道就只剩下“优美的舞蹈”了吗?本文即是困惑之余的探索与反思,谨请读者和邹先生审阅、批评。
一、行当与人物性格
要讨论戏曲应该演行当还是演人物的问题,首先得了解什么是行当?行当是如何产生的?
行当其实就是脚色分类。行当的本义是行业、职业。社会上有各行各业,戏曲里有各类脚色,所以习惯上往往将“行当”与“脚色”连称为“脚色行当”。应当注意的是,脚色和角色不同。角色就是剧中人,而脚色,简单说就是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丑。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搞清楚角色和脚色的关系,也就不难明白戏曲究竟是演人物还是演行当了。
中国早期戏剧只有脚色而没有行当,这是因为,早期戏剧中的脚色很少,不需要分类。唐代参军戏只有参军和苍鹘两个脚色,宋杂剧、金院本出现了“五花爨弄”,有五个脚色,都不必分类。到了金元杂剧和宋元南戏,情况就不同了。仅元刊杂剧中出现的脚色和准脚色名称就有近二十种之多,这就需要分类。夏庭芝《青楼集》、王骥德《曲律》虽未使用“脚色行当”的说法,但都把元杂剧脚色分为末、旦两大类,已明确具有分类意识。《扬州画舫录》总结清中叶昆曲的脚色行当为“江湖十二脚色”,并提出“男脚色”、“女脚色”两大类别,这与夏庭芝、王骥德的说法一脉相承。此后地方戏兴起,各声腔剧种间的脚色行当大同小异,总的趋势是,脚色越来越多,行当划分越来越细密。
不难理解,戏曲要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一个演员要扮演许许多多的角色(剧中人),其难度可想而知。而脚色行当的出现,就可以把所有的人分成不同的类别。一个演员,只要掌握了其中一个行当的演技(程式),就可以在戏台上立足了。可以说,戏曲表演水平的日益精致化、复杂化,正是脚色行当划分的内在动力。
同时,脚色行当的划分,与剧中人的身份、性格息息相关。不用说,无论是行当还是程式,都是动态的而非凝固的。古代艺术家早已意识到脚色行当与人物性格的内在联系,从而不断发展出新的行当,使行当的划分,即类型化的形象系统与性格化的剧中人交融在一起。
例如昆曲中的生行,后来发展出正生、小生、大冠生、小冠生、巾生(扇子生)、穷生(鞋皮生)、雉尾生等行当。顾名思义,大冠生头戴冠冕和髯口,常常扮演中年以上的皇帝和官员,例如《长生殿》中的唐明皇、《千钟禄》中的建文帝等,“表演要求气度恢弘,功架持重大方”;小冠生又称“纱帽小生”,无髯口,多扮演青年官员,如《荆钗记》中的王十朋、《金雀记》中的潘岳等,“表演讲究在儒雅飘逸的基调中透出气宇轩昂的神态”;雉尾生以帽插雉尾得名,多扮演雄姿英发的青年武将,如吕布、周瑜等,“要求嗓音清亮激越,并常伴以舞动翎子来表现脚色(应为角色——引者注)心情和神态”。值得提出的是,脚色行当及其装扮与剧中人的对应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剧中人年龄、身份的变化相应发生变化。例如《琵琶记》中的蔡伯喈原归小冠生,做官以后改为大冠生应工;《长生殿》中的唐明皇原戴黑髯,但《哭像》一出戴花三,“以展示他悲痛凄怆的衰年形象”。
昆曲中的旦行,竟然可分出九种不同的旦脚,从九旦起,八旦、七旦、六旦、五旦、四旦、作旦、正旦到老旦止,一共九个行当。据宁波昆剧老艺人介绍,九旦多演宫女、丫鬟,如《西厢记》“游殿”中的红娘;八旦可以扮演《玉簪记》“秋江”中的陈妙常、《西厢记》“游殿”中的莺莺;七旦又称“花旦”,可扮演《西厢记》“跳墙”中的红娘、《义侠记》“投帘”中的潘金莲;六旦要求“对不同性格、不同处境的剧中人物都需要有一番揣摩功夫,才能适合剧情”,例如扮演《水浒记》“活捉”中的阎婆惜、《白蛇传》“断桥”中的青蛇、《玉簪记》“偷诗”中的陈妙常等;五旦的特点是“稳重文静,眼风生动”,例如“和番”中的王昭君、《长生殿》中的杨贵妃以及《义侠记》“别兄”中的潘金莲等。作旦即“闺门旦”。正旦、老旦大家都很熟悉,无需饶舌。
值得注意的是,在宁昆这里,同一个剧中人,如红娘、莺莺、潘金莲、陈妙常,在不同的场合(折子),竟然用不同的行当扮演。可见戏曲演出中行当与剧中人的处境、性格、心理的对应,达到了多么细密的程度。另外旦行中的四旦,又称“刺杀旦”,从《一捧雪》“刺汤”中的雪艳娘、《铁冠图》“刺虎”中的费贞娥、《渔家乐》“刺梁”中的邬飞霞发展而来。从一个人物、一个动作、一个身段,可以发展成一个行当。这样的例子,足以说明行当与剧中人的关系。
本来,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不可代替的,然而却又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别人往往可以成为自己的镜子和影子。戏曲行当与人物(剧中人)的关系,上升到哲学高度看,就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一般中有个别,个别中也有一般,行当中已经包含了人物性格。所以,中国戏曲不是不演人物,而是通过行当演人物。行当只不过是一个中介、一种手段而已。要是把演行当与演人物对立起来,甚至把演行当当成了戏曲表演的主要目的,那就无异于舍本逐末、缘木求鱼。
二、戏曲史上扮演人物的传统
戏曲人物是如何产生的?当然首先来自作家笔下。宋金杂剧、宋元南戏以来,有多少戏曲人物让人们记忆犹新。比如,关汉卿笔下的窦娥、谭记儿、赵盼儿,王实甫笔下的张生、莺莺和红娘,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柳梦梅、春香、陈最良,高则诚笔下的蔡伯喈和赵五娘等等。宋元南戏开创了成熟戏曲扮演人物的传统。众所周知,早期南戏多以主人公姓名作为剧目名称,如《赵贞女》、《王焕》、《张协》、《王魁》、《刘文龙》等等。难以想象,表演这些剧目的演员不扮演剧中人而只表演行当。据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宋末元初温州乐清县一位恶僧祖杰,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于是有人把他的劣迹编成戏文,广事宣传,使得祖杰最终被官府处死。这个戏的演出效果竟能造成一种“众言难掩”的舆论,可见它一定是演人物的。钱南扬据此把这个戏命名为《祖杰》。
金元杂剧虽说以曲为本位,但其本质也是扮演人物的。南戏《错立身》写官宦子弟完颜寿马自夸会“做杂剧”,唱【鬼三台】一曲:
我做《朱砂担浮沤记》;《关大王单刀会》;做《管宁割席》破体儿;《相府院》扮张飞;《三夺槊》扮尉迟敬德;做《陈驴儿风雪包待制》;吃推勘《柳成错背妻》;要扮宰相做《伊尹扶汤》;学子弟做《螺蛳末泥》。
明中叶以后,传奇(含昆曲)扮演人物、产生轰动演出效果的记载比比皆是。其中颜容扮演《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他为深入体会角色、揣摩剧中人心情,反复对镜练习,最终使台下千百人哭皆失声的事迹,已为戏曲史研究者津津乐道。此外,吴郡演员陈明智因演《千金记》中的楚霸王而创立“起霸”的程式;申时行家班男旦张三,“(演)红娘,一音一步,居然婉弱女子,魂为之销”;杭州女演员商小玲因扮演杜丽娘入戏过深,伤心而死;海盐演员金凤因长期服侍严世蕃,世蕃死后,金凤在《鸣凤记》中扮演他而惟妙惟肖。这些例子,都为人熟知。更典型的是金陵回族演员马伶,在一次《鸣凤记》竞演中输给了另一戏班的李伶,因耻居其下,苦练三年后又在《鸣凤记》中扮演严嵩,“李伶忽失声,匍匐前,称弟子”。当有人问马伶何以为师时,马伶回答:“我闻今相国某者,严相国俦也。我走京师,求为其门卒,三年日侍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为师也。”(11)
有人认为,戏曲演人物是受了西方话剧的影响,这完全是误解。王骥德《曲律》“论引子”云:
引子,须以自己之肾肠,代他人之口吻。盖一人登场,必有几句紧要说话,我设以身处其地,模写其似,却调停句法,点检字面,使一折之事头,先以数语该括尽之,勿晦勿泛,此是上谛。《琵琶》引子,首首皆佳,所谓开门见山手段。《浣纱》如范蠡而曰“尊王定霸,不在桓文下”,施之越王则可,越夫人而曰“金井辘轳鸣,上苑笙歌度,帘外忽闻宣召声,忙蹙金莲步”,是一宫人语耳!(12)
“以自己之肾肠,代他人之口吻”,这或许就是戏剧文体为“代言体”说法的滥觞。凡戏剧,无论是中国戏曲还是西方话剧,其本质都是角色扮演,其文本都以代言体为主,概莫能外。“设以身处其地,模写其似”,就是戏中曲辞要符合剧中人身份。王骥德认为,戏曲剧本从引子开始,就要“调停句法,点检字面”,“勿晦勿泛”。他批评《浣纱记》中越王夫人的唱词不符合她的身份,而只“是一宫人语”。这一主张,历历在目,言犹在耳,堪称是指导戏曲创作和戏曲表演的金玉良言。
在当时,王骥德的主张不是孤立的。《元曲选》的编者臧懋循说:“行家者随所妆演,无不摹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而几忘其事之乌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1 )臧氏认为当行的戏曲演员必须懂得体会剧中人所处情景。他所说的“宛若身当其处”与王骥德主张的“设以身处其地,模写其似”毫无二致。另一著名戏剧家孟称舜在谈到戏曲的创作和演出时也说:“学戏者不置身于场上,则不能为戏;而撰曲者不化其身为曲中之人,则不能为曲。”在他看来,当行的剧作应该是:“笑则有声,啼则有泪,喜则有神,叹则有气。”(14)
李渔的《闲情偶寄》在王骥德、臧懋循、孟称舜等人的基础上,详细阐明了编剧、演剧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李渔从自己的戏曲创作实践出发,归纳出“代言体”戏曲创作须“设身处地”,先代人立心,后代人立言,方能达到“说一人,肖一人”的充分性格化的境界。他说:
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篯之上……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无论立心端正者,我当设身处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当舍经从权,暂为邪辟之思。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果能若此,即欲不传,其可得乎?(15)
作为一位精通舞台演出的戏曲作家兼理论家,李渔当然不会忽略行当与程式的重要性。但他并不认为行当与人物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在他看来,行当已经蕴含有人物性格,而人物则是行当、程式的细化。他先说:“在花面口中,则惟恐不粗不俗;一涉生旦之曲,便宜斟酌其词。无论生为衣冠、仕宦,旦为 、夫人,出言吐词,当有隽雅舂容之度。即使生为仆从,旦作梅香,亦须择言而发,不与净丑同声。以生旦有生旦之体,净丑有净丑之腔故也。”接着他进一步从行当、程式说到人物:“填词义理无穷,说何人肖何人,议某事切某事,文章头绪之最繁者,莫填词若矣。予谓总其大纲,则不出‘情’、‘景’二字。景书所睹,情发欲言,情自中生,景由外得,二者难易之分,判如霄壤。以情乃一人之情,说张三要像张三,难通融于李四;景乃众人之景,写春夏尽是春夏,止分别于秋冬……如前所云《琵琶·赏月》四曲,同一月也,牛氏有牛氏之月,伯喈有伯喈之月。所言者月,所寓者心。牛氏所说之月,可移一句于伯喈?伯喈所说之月,可挪一字于牛氏乎?夫妻二人之语,犹不可挪移混用,况他人乎?”(16)此处所云“情乃一人之情,说张三要像张三,难通融于李四”,就是高度的个性化;“景乃众人之景”,就是程式化。所以,在类型化中追求个性化,是李渔戏曲理论中的核心理念之一。
王骥德和李渔等人的主张,是宋元以来戏曲创作和表演实践的总结和理论升华。可见,中国古代,早已形成了进入角色、体验人物、扮演剧中人的演剧传统和表演理论,这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早了几百年。
三、谭鑫培、杨小楼如何演人物?
晚清以来兴起的皮黄(京剧)在扮演人物、塑造人物性格和舞台形象方面,比昆曲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邹元江批评梅兰芳“从一开始就不真正明白如何理解‘京剧精神’”(17),这里拟简单介绍梅兰芳之外谭鑫培与杨小楼如何演人物。
谭鑫培活跃在清末民初的北京剧坛,有可能受到西方戏剧的影响,特别是他的晚年,曾经听齐如山介绍西方戏剧。但毫无疑问,使谭鑫培受益更大、更多的,是他深厚、精湛的传统戏曲表演功底和他对戏剧本质的理解。陈彦衡《旧剧丛谈》记云:
名角演剧,首重作工,盖有作工而后唱、念、身段始有精彩。作工者,表情之谓也……谭鑫培演孔明有儒者气,演黄忠有老将风,《胭脂褶》之白槐,居然公门老吏;《五人义》之周文元,恰是市井顽民。流品迥殊,而各具神似。由其平日于各色人等之举止语言,无不细心体察,刻意揣摩,故其扮演登场,能随时变态,移步换形……余尤爱其《状元谱》一剧,见大官始而讶、继而怒、怒而至于打,如文章之由浅入深,画家之由淡而浓,步步引人入胜。而盛怒之下,态度深稳,身分尤高,妙处全在痛恨子侄不肖,虽狠心责打,实具爱怜之苦衷。其斥大官,追念先嫂,声泪俱下,令观者友爱之心油然而生,此岂可以寻常作工目之耶?(18)
这样的做功与演出效果,岂是听几次演讲所能促成的?其关键就在于:“平日于各色人等之举止语言,无不细心体察,刻意揣摩,故其扮演登场,能随时变态,移步换形。”如果说,熟练地掌握某一行当的表演程式可以做到形似的话,那么,善于揣摩各色人等的举止与形态,并且能够结合剧情,用身段和程式惟妙惟肖地表演出来,才能做到神似。换言之,一个戏曲演员,即使身上的功夫再好,如果不能演出他所扮演的“那个人”来,就是只有骨架,没有灵魂。
苏雪安《京剧前辈艺人回忆录》中记述,谭鑫培一次演《洪羊洞》,当剧中八贤王问杨延昭“御妹丈此病从何而起”时:
杨延昭照例应以手击桌摇首慨叹地叫出一声“千岁爷”来。谭氏当然也是那样演,可是他的眼光极为传神,他在摇头叹息之前,先把两只眼睛凄惶地望着八贤王半晌,然后才缓缓地叹出声来。等到念“千岁爷”三个字的时候,眼眶确实是红了,可是不掉眼泪……他这种神气,不但抓住了台下观众,把台上的八贤王也看傻了!(19)
这段记述,生动地展示出谭鑫培演出时的身段、眼神和舞台效果。同样的台词,同样的动作,谭氏演来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对剧中人当时情景的揣摩与体验。长期以来,不少人把写实与写意、表现与体验对立起来,这完全是误解。戏曲的四功五法、手眼身法步,是表现人物的重要手段,而能把“眼神”运用到家的艺术家却是凤毛麟角。谭鑫培就是这样的大艺术家。苏雪安接着叙述道:
谭氏演《洪羊洞》)在二次被太君等人唤醒以后所唱的散板,真是一唱三叹,每唱一句,随着他的神气,左顾老母,右恋妻子,怀抱宗保,种种情态,同真人真事一样,可惜我的笔尖上无法形容。(20)
这里的所谓“真人真事”,当然是艺术化、戏剧化了的真人真事,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是用戏曲手段表现出来的“真实”。戏曲如果只演行当而不演人物,就不会有这样的艺术真实。中国戏曲与西方话剧当然是有区别的,但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表现手段不同,而不在于对戏剧本质的认识有什么不同。
齐白石晚年总结作画原则时说过一句名言:“作画在似与不似之间为妙,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21)这一原则也可以用于戏剧,尤其可用于戏曲。谭鑫培就是能精准把握这一原则的戏曲大家。他常说:“演唱时要逼真,但过分逼真也会缺乏意趣。所谓‘不像不是艺,全像不算艺’。”(22)据说,一次汪桂芬微服往观谭鑫培演《卖马》,只见谭氏容貌清癯,声复悲壮,舞锏一段把英雄末路、侘傺无聊之状发挥到极致,汪桂芬不禁惊叹失声:“是天生秦叔宝也!竖子当成名矣!”(2 )谭鑫培扮演《李陵碑》中的杨业,当唱到“遍体飕飕”时,用双手一抱肩,不见头摇,只见头上绒球抖动,令人有寒风瑟瑟之感。看过这一表演的梅兰芳说:“谭老先生的《李陵碑》,在唱反调以前,出场时冷的动作如同真的一样。我是个演员,在六月伏天时坐在台下看,却觉身上发冷。”(24)这就是戏曲演员的本事,不仅能用自己的表演使人物的心灵得以外化,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打破时空的限制,化无为有,变夏为冬。这就是戏曲的神韵和精髓。学到这一点,才掌握了戏曲表演的真谛,而脚色行当的程式、身段、唱念,虽然对于一般演员来说也很重要,但要是与大艺术家所掌握的用戏曲手段“很切合剧情地扮演那个剧中人”比起来,终究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谭鑫培的出色表演,把皮黄戏艺术推到了新的高峰,也引领了用戏曲手段表演剧中人的时代风尚。仅以京剧界而言,杨小楼、王瑶卿、余叔岩、梅兰芳、萧长华、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周信芳、马连良、谭富英等艺术家无不效仿,而且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限于篇幅,这里只借助于前辈艺人和学者的回忆与描述,简单谈谈著名武生杨小楼的表演艺术。
和文戏相比,武戏主要用武打场面吸引观众,更容易流于千人一面。但在谭鑫培的教诲与影响下,杨小楼追求“武戏文唱,因此抓住了人物的感情”(25)。例如《野猪林》中的林冲发配,一般人演来,是倒在地上,大甩水发,能博得不少观众的掌声。但杨小楼认为,林冲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不能向解子苦苦哀告,露出一副可怜相。他此处的表演是:“被解子打得趋步坐地,紧跟着咬咬牙根挺起身来,虽然戴着手铐,走左右倒腿蹦子,仍然显出他是个英雄汉,不失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身份。”(26)杨小楼扮演《长坂坡》中的赵云,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在《掩井》一场,杨小楼的演法是:
赵云抬起双手刚要接过夫人递过来的“喜神”阿斗,发觉夫人行动反常,倒吸一口凉气,连连摆手作揖不接阿斗。他一面催促夫人上马,一面用眼四下了望,怕有曹兵发觉袭来。糜夫人死意已决,干脆将阿斗放在地上。阿斗啼哭起来,赵云这才不得已俯身抱起。糜夫人情急智生,诓赵云说:“看那旁曹兵来了。”赵云回头不见曹兵,情知不妙,一个急转身,蹉步窜上前去,想用手抓住已经登上井台的夫人,不想只抓住帔衣,加以向后用力过猛,身体失掉平衡,这才以旋风似的起“蹦子”,表示仓惶间站立不稳,用以表露人物惊愕、紧张的心情。(27)
可以说,自觉地运用武生行当的表演程式为剧情服务,为刻画人物性格服务,在扮演人物中创造出新的程式和手段,是杨小楼成为一代武生宗师的唯一奥秘。
四、行当和曲意
邹元江说:“中国戏曲艺术最发达、也最具审美意味的就是‘行当’的程式丰富性,因此,消解了‘行当’也就消解了中国戏曲艺术极为成熟丰富的‘程式性’。这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戏曲艺术的独特存在样式。”接着,他批评梅兰芳“从一开始就不真正明白如何理解‘京剧精神’,或戏曲艺术的美学精神”(28)。那么,什么是“京剧精神”或“戏曲艺术的美学精神”呢?这种“精神”是不是就是行当或程式呢?是谁主张“消解行当”呢?邹元江都没有明说。
众所周知,过去梨园界在形容一个演员戏路宽、能跨声腔、跨行当的时候,常常用“文武昆乱不挡”来形容。仅以京剧界而言,“程长庚、余三胜、王九龄、徐小香、胡喜禄、徐宝成、何桂山、俞菊笙、杨隆寿、时小福、梅巧玲、余紫云、谭鑫培、王福寿、王长林、钱金福、余玉琴、陈德霖等,都够得上‘文武昆乱一脚踢’”(29)。光绪年间,梅巧玲和余紫云将青衣和花旦的表演特长加以融合,创造出“花衫”这一新的行当。著名京剧演员谭元寿讲到他曾祖父谭鑫培“善于根据剧情需要刻画人物”,把花脸唱法、老旦腔,甚至京韵大鼓的唱法都“化到老生唱腔里”( 0)。谭鑫培原来唱武戏,后来唱老生,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武戏的东西揉到文戏里去”;武生杨小楼则是在武戏里揣摩剧情和人物,努力做到“武戏文唱”。而粤剧干脆完全打破了文和武的界限,创立了特色鲜明的“文武生”行当。凡此种种,都说明各行当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强调了行当的不可消解之后,邹元江还批评梅兰芳对“唱词宾白的意义的‘关注’则更是对昆曲审美趣味的偏离”( 1)。邹元江在大段征引梅兰芳本人对昆曲《游园惊梦》曲辞反复钻研并向文人请教的过程后提出:梅氏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近代西方的话剧思维方式,尤其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思想”。邹氏认为:“戏曲的身段动作不是都能在‘合道理’、在‘实对’的意义上来解释的”,“词义与表达词义的身段动作并不是相同一的,而是相间离的”,“过去时代的戏曲艺术家大多没有文化,因此,唱词文字的意义对他们而言,其实只是说戏的师傅所讲的故事梗概而已,顶多再加上故事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区分”。
那么,戏曲演员要不要弄懂曲辞的文意呢?梅兰芳的做法是不是“话剧思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思想”呢?不妨先来看看李渔的论述。《闲情偶寄·演习部》“授曲第三”专设“解明曲意”一节,全文如下:
唱曲宜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节也。解明情节,知其意之所在,则唱出口时,俨然此种神情,问者是问,答者是答,悲者黯然魂消而不致反有喜色,欢者怡然自得而不见稍有瘁容,且其声音齿颊之间,各种俱有分别,此所谓曲情是也。吾观今世学曲者,始则诵读,继则歌咏,歌咏既成而事毕矣。至于“讲解”二字,非特废而不行,亦且从无此例。有终日唱此曲,终年唱此曲,甚至一生唱此曲,而不知此曲所言何事,所指何人,口唱而心不唱,口中有曲而面上、身上无曲,此所谓无情之曲,与蒙童背书,同一勉强而非自然者也。虽腔板极正,喉、舌、齿、牙极清,终是第二、第三等词曲,非登峰造极之技也。欲唱好曲者,必先求明师讲明曲义。师或不解,不妨转询文人,得其义而后唱。唱时以精神贯串其中,务求酷肖。若是,则同一唱也,同一曲也,其转腔换字之间,别有一种声口,举目回头之际,另是一副神情。较之时优,自然迥别。变死音为活曲,化歌者为文人,只在“能解”二字,解之时义大矣哉!( 2)
可见,梅兰芳的做法,完全符合李渔的演剧主张。在李渔看来,戏曲不是清曲,更不是“蒙童背书”;相反,只有“解明曲意”才能“以精神贯串其中”,唱出剧中人应有之情感。昆曲词意艰深,梅兰芳弄不懂而向文人请教,再把自己的理解化为身段,这怎么是“偏离了昆曲的审美趣味”了呢?的确,古代戏曲演员多不识字,师傅怎样教徒弟怎样唱,有的唱了一辈子也不知道所唱的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才是“昆曲的审美趣味”?
邹元江罗列了梅兰芳对《游园惊梦》唱词身段的几处解释,批评梅兰芳的理解“太写实对应”,是“话剧式的真实对应”,“与中国戏曲艺术更加追求意象生成和意境创造的审美精神是背道而驰”;邹元江还使用了“真是匪夷所思”,“让人难以置信”这样的表述。例如他说梅兰芳:
言“闭月”,就做“手比月亮,向左高看”身段,言“花愁颤”,就做“用扇略抖”身段,言“画船”,就做“各把扇子倒拿着,做出摇船的姿势”身段——这也太写实对应了!最让人难以理喻的是梅兰芳对这些对应身段的解释。杜丽娘的唱词“没乱里春情难遣”一句梅兰芳说:“‘难遣’,伸右手食指,在桌上慢慢画圈。”对这个身段梅兰芳的解释是:“这个动作很细致地形容她的心里烦闷,难以排遣。”——这从何说起!做“伸右手食指,在桌上慢慢画圈”身段就是“很细致地形容”了杜丽娘的“心里烦闷,难以排遣”的状态,这真是匪夷所思!
这段文字可分作前后两段,前边是批评梅兰芳的身段“太写实对应”,后来却又说用右手画圈来形容杜丽娘的心情“匪夷所思”。也就是说,一边强调身段与唱词不能够写实对应,一边又对不对应心理描写的身段大加指责。这遵循的究竟是什么逻辑呢?不用手画圈,怎样表现杜丽娘的心态呢?请邹先生指教。
昆曲表演艺术在明末清初有一个大的飞跃,入清以后越发精致,其唱词、身段也与剧情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这就需要对其规律加以总结。于是,《乐府传声》、《梨园原》、《明心鉴》、《审音鉴古录》以及一批昆曲身段谱应运而生。周贻白说《明心鉴》的命义为:“这是指一个演员要想把他所扮饰的人物演好,必须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他在剧情中所处的地位,先弄明白。然后根据自己的体会,从内心出发,来演出这个人物在剧中的经历。”( )此言甚是。相比而言,《审音鉴古录》不仅曲文齐备,而且为曲词标明叶韵、板拍,在关键处纠正读音错讹,并佐以工尺谱,尤为突出的是对“穿关”、“科介”进行阐述,并用眉批、旁注对演员的身段、动作加以详细说明,从而成为指导昆曲乃至戏曲表演的教科书。
《审音鉴古录》在《荆钗记》“舟中相会”原曲牌【园林好】、【江儿水】中加进大量的动作、心态提示。例如在老旦唱“止不住盈盈泪瀼,瞥见了令人感伤”旁注:“老旦手颤哭咽泪落杯中放介”,在贴唱“细把他仪容比方,细将他行藏酌量”旁注:“贴细认老旦介”。有学者指出:这“很好地把握了角色的情感表情”,显示出《审音鉴古录》“对角色创造的理解与重视”( 4)。这当然是没错的,而这恰恰就是邹元江所批评的唱词与身段动作的“写实对应”。《荆钗记·绣房》中,小旦唱【一江风】:“绣房中,袅袅香烟喷,翦翦轻风送。但晨昏问寝高堂,须把椿萱奉。忙梳早整容,忙梳早整容。惟勤针指功,怕窗外花影日移动。”《审音鉴古录》在唱词旁的动作提示却是:“先揭盖,后倚绣床忙。开针线书,剪去针尾线,提线穿针,理丝抽结,形容女子刺绣状。”有学者指出,这里的“动作并不完全是在阐述唱腔,它表现的是人物的闺阁生活动作。从揭盖、翻书到穿针、引线,俨然一套刺绣的程式性动作,今日的《拾玉镯》等剧似乎能从中找到前世的影子”( 5)。这个说法有道理。戏曲表演中的唱词和动作,有时候对应,有时候不对应,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唱词本身有的较实,有的较虚,如此而已。
昆曲乃至戏曲的身段、动作,是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手段之一。经过历代戏曲表演艺术家的不断提炼,形成了诸如起霸、走边,开门、关门,上楼、下楼,划船、坐轿等程式,观众一望可知其表达的意思。在载歌载舞的场合,也应当尽可能与唱词对应,使观众明白其意而不至于如坠五里雾中。老一辈昆曲表演艺术家丁兰荪( 7)在表演《思凡》中“十万八千有余零”这句唱词时,“在前上场角以拂尘柄与左手合搭成十字状,然后左手接住拂尘柄,右手伸食、拇指两指作八字状”( 6),即为显例。
梅兰芳“对昆曲有深厚的感情,下过长期的苦功,功底极深”( 7)。梅氏十一岁第一次登台,演的就是昆曲《长生殿》中《鹊桥密拼》一出的织女。成角儿后常演的有《雷峰塔》中的“水斗”、“断桥”,《西厢记》中的“佳期”、“拷红”,《风筝误》中的“惊丑”、“前亲”、“后亲”,《玉簪记》中的“琴挑”、“问病”、“偷诗”,《渔家乐》中的“藏舟”,《铁冠图》中的“刺虎”等。尤其是在《游园惊梦》中扮演杜丽娘,更是昆曲剧目中的极品。
白先勇在话剧《游园惊梦》里,借剧中人顾传信之口说:“戏院里,昆曲的戏码都变成冷门儿啦。这要等到梅先生出来,才把几出昆曲又唱红了。尤其是他那出招牌戏《游园惊梦》,让他唱得大红特红,梅先生的昆曲艺术在这出戏里也就达到极致啦。”赖夫人回应说:“顾老师,您到底是行家。这句话说到咱们心坎儿上来了。梅兰芳的这出《游园惊梦》,确实是昆曲里的无上珍品!我不知看他演过多少回啦,真是百看不厌!”( 8)这应当也是白先勇自己的切身感受吧?后来白先勇不遗余力地打造青春版《牡丹亭》,应当就是从这里受到的启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梅兰芳不是昆曲精神的违背者,而恰恰是昆曲精神的忠实继承者和实践者。
在昆曲中,《游园惊梦》的表演难度很大。剧中女主角官宦家千金的身份和春心初萌的心理,使她的思想感情非常细腻,表面上深藏不露,实际上暗流涌动,这对演员表演技巧的要求很高。正如俞振飞所说:
《惊梦》一场,因为表现的不是普通的梦境,似真非真,似幻非幻,似虚非虚,似实非实,所以杜丽娘的表演也要与此相适应,既不能过实,又不能过虚。过实则易于损伤梦的意境,过虚又极易流于轻浮,最好的表演是在缠绵中表现出一些飘忽感。我演此戏几十年,对手也是数以十计,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象兰芳同志那样演得恰到好处。( 9)
俞振飞还说:“每次我与他合作演《惊梦》,一接触他那明如秋水的双瞳,整个身心都会感到很大的震动,好象一股巨大的暖流贯穿全身。”“(梅兰芳)把人物在各个阶段的不同心情和感受,贯穿在全部唱、念、身段和面部表情中”。俞振飞还毫不吝啬地使用“浑若天成”、“水 融”、“丝丝入扣”、“浑然全似”、“严丝密缝”、“炉火纯青”、“令人荡气回肠”这些字眼称赞梅兰芳。可见,两位艺术家的心是相通的。
梅兰芳不是不可以批评,毕竟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但允许批评也应当允许回应和反批评。本文不拟对邹元江的批评一一回应,而是就戏曲是演行当还是演人物的问题进行必要的讨论。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戏曲表演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具有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意义。主张戏曲只演行当就不要表情,反之,主张戏曲不能只演行当还要演人物,就一定要有表情。主张戏曲只演行当就不需要弄懂唱词的意义,主张戏曲既演行当更重要的是演人物就必须知道唱词的意义。这道理再明白不过。
陈建森曾经对戏曲只演行当不演人物的观点提出过质疑和商榷(40),但邹元江在回应中依然声称:“戏曲演员的表演不是‘表演角色’,而是‘表演行当’,这恰恰是由戏曲艺术自身的审美特性规定的。”(41)尽管邹氏所说的“戏曲艺术自身的审美特性”究竟指什么,我们不清楚,但却清楚地记得:被公认为“伶界大王”的谭鑫培曾被汪桂芬称作是“天生的秦叔宝”,杨小楼曾被观众誉为“活赵云”,盖叫天被称作“活武松”,著名潮剧演员洪妙被称作“活令婆”(令婆即佘太君),著名越调演员申凤梅被称为“活诸葛”,等等。这些来自艺术家和观众的声音,有力地回答了戏曲究竟是演人物还是演行当的问题。正如梅兰芳所说:“到底赵云是个什么长相,有谁看见过的吗?还不是说他(杨小楼——引者注)的气派、声口、动作、表情,样样吻合剧中人的身份。台下看出了神,才把他当作理想中的真赵云的吗?”(42)梅兰芳一语中的:只有演人物才有“神”。
总之,脚色行当的划分是中国戏曲不同于许多外国戏剧的一个特征,但并不是束缚演员表演的枷锁,各行当间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近代以来行当划分愈来愈细的倾向,体现了戏曲对表演个性化人物的追求愈来愈具有自觉意识。因而,把演人物和演行当对立起来是十分不妥当的。
注释:
邹元江的这些论著包括:《中西戏剧审美陌生化思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梅兰芳的“表情”与“京剧精神”》,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2期;《谁是“梅兰芳”?》,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2期;《对“梅兰芳表演体系”的质疑》,载《艺术百家》2009年第2期;《解释的错位:梅兰芳表演美学的困惑》,载《艺术百家》2008年第2期;《从阿甲对梅兰芳的批评看建国之初“戏改”运动的问题》,载《戏曲艺术》2008年第2期;《从周信芳与应云卫的合作看“海派京剧”的本质》,载《戏剧艺术》2007年第4期;《脆弱的 :体验与表现的统一》,《戏曲研究》第76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从梅兰芳对游园惊梦的解读看其对昆曲审美趣味的偏离》,载《戏剧》2010年第4期等。
笔者从中国知检索到的直接回应邹文的三篇文章是郭月亮《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戏曲艺术的审美精神”?——对邹元江先生批评阿甲的思考》,载《中国戏剧》2009年第9期;龚和德《怀念阿甲老师——兼与邹元江先生商榷》,载《中国戏剧》2008年第5期;罗丽《也谈戏曲的“表情”——与邹元江先生商榷》,载《南国红豆》2010年第4期。此外陈建森《戏曲本体与生成的探究之途——评邹元江〈中西戏剧审美陌生化思维研究〉》(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8期)一文,部分赞成邹元江的观点,但也对邹氏只演行当的观点进行商榷,并引起了邹氏的反批评,参见本文“结语”。
42)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全集》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页,第 75页。
17)(28)邹元江:《中西戏剧审美陌生化思维研究》,第 2页,第 页,第 页。
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2页。
洪惟助主编《昆曲辞典》,(台北)“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02年版,第558、559页。
参见《宁波昆剧老艺人回忆录》,内部资料,苏州市戏曲研究室196 年,第页。
参见钱南扬《戏文概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页。
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4页。
潘之恒:《鸾啸小品》,汪效倚辑注《潘之恒曲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1 6页。
11)焦循:《剧说》,俞为民等编《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 集,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页。
12)王骥德:《曲律》,《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2集,第97页。
1 )臧懋循:《元曲选后集序》,《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1集,第621页。
14)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序》,朱颖辉辑校《孟称舜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56页。
15)(16)( 2)李渔:《闲情偶寄》,《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1集,第页,第 页,第 16页。
18)陈彦衡:《旧剧丛谈》,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
19)(20)(25)苏雪安:《京剧前辈艺人回忆录》,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第5 页,第54页,第161页。
21)朱天曙选编《齐白石论艺》,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页。
22)李名正、李卓敏:《谭鑫培的唱》,周育德主编《说谭鑫培》,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
2 )曹绣君:《清代声色志》,《古今情海》“附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24)陈彦衡订谱《谭鑫培唱腔集》第 辑,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第54页。
26)(27)曲六艺:《一代武生宗师杨小楼》,载《戏曲艺术》198 年第4期。
29)张文瑞:《文武昆乱不挡》,载《文史知识》201 年第9期。
0)谭元寿口述、刘连群整理《谭派艺术溯源》,《说谭鑫培》,第51页。
1)邹元江:《从梅兰芳对〈游园惊梦〉的解读看其对昆曲审美趣味的偏离》,载《戏剧》2010年第4期。以下所引邹元江语均见此文。
)周贻白:《戏曲演唱论著辑释》,中国戏剧出版社198 年版,第177页。
4)胡亚娟:《〈审音鉴古录〉中“批录”的美学思想》,载《文化遗产》2008年第 期。
5)杨玉:《论〈审音鉴古录〉对角色创造的理论阐释》,载《艺海》2014年第9期。
6)《丁兰荪〈思凡〉身段谱述例》,《昆曲辞典》,第640页。
7)( 9)俞振飞:《无限深情杜丽娘——谈谈兰芳同志在〈游园惊梦〉中的表演艺术》,载《上海戏剧》1962年第2期。以下所引俞振飞语均见此文。
8)白先勇:《游园惊梦》,《白先勇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40)陈建森:《戏曲本体与生成的探究之途——评邹元江〈中西戏剧审美陌生化思维研究〉》,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8期。
41)邹元江:《迂回进入 返本开源——对陈建森批评的回应》,载《文艺研究》201 年第7期。
康保成, 陈燕芳. 戏曲究竟是演人物还是演行当?——兼驳邹元江对梅兰芳的批评[J]. 文艺研究, 2017(7): 1.
(: )
晋城哪家医院治疗白癜风如何给小孩健脾
妇科千金片售价

- 上一篇:北京哪家有卖gr集成吊顶生存
- 下一篇:新型制药压片机优势突出促进新技术支持化工区域
-
阿拉斯加犬患上疖螨全身痒求治疗方法位置
阿拉斯加犬得了疖螨浑身痒.把毛剃掉了发现大量皮肤表层有结痂和皮屑.宠物医生确诊疖螨.现在打针.药浴和外用药都在使用.同时疖螨也传染给了我和老...[详细]
2022-06-03
-
阿拉斯加犬患上急性肠炎四肢无力怎么办位置
两个月大阿拉斯加犬,一个多星期前得过一次急性肠闻炎,也就一天就好了,之后就出现了四肢无力的情况,开始还能艰难的走几步,可是现在基本只能爬了,一...[详细]
2022-06-03
-
阿富汗猎犬喜欢抓脸的原因及解决方法位置
阿富汗猎犬拉肚子,大便稀中带有水,饮食正常,怕冷,不爱运动,精神不好,怎么办肥肥雨燕:犬拉肚子的原因很多,突然改变饲料,吃多了,吃了不...[详细]
2022-06-03
-
阿富汗猎犬剪毛教学正确美容好精神位置
阿富汗猎犬拉肚子,大便稀中带有水,饮食正常,怕冷,不爱运动,精神不好,怎么办肥肥雨燕:犬拉肚子的原因很多,突然改变饲料,吃多了,吃了不...[详细]
2022-06-03
-
阿富汗猎幼犬易患肠胃病如何预防位置
阿富汗猎幼犬的肠胃还有没有发育完全,所以肠胃功能比较差。给阿富汗猎幼犬吃的食物不卫生或者坏了,就会导致爱犬患上肠胃疾病,阿富汗猎幼犬就...[详细]
2022-06-03
-
异国短毛猫配种方法位置
异国短毛猫配种方法异国短毛猫配种方法养宠物的朋友大多都是因为喜欢这种小动物,像养外国进口的短毛猫也是一样的。只是目前我国养进口宠物的朋...[详细]
2022-06-03